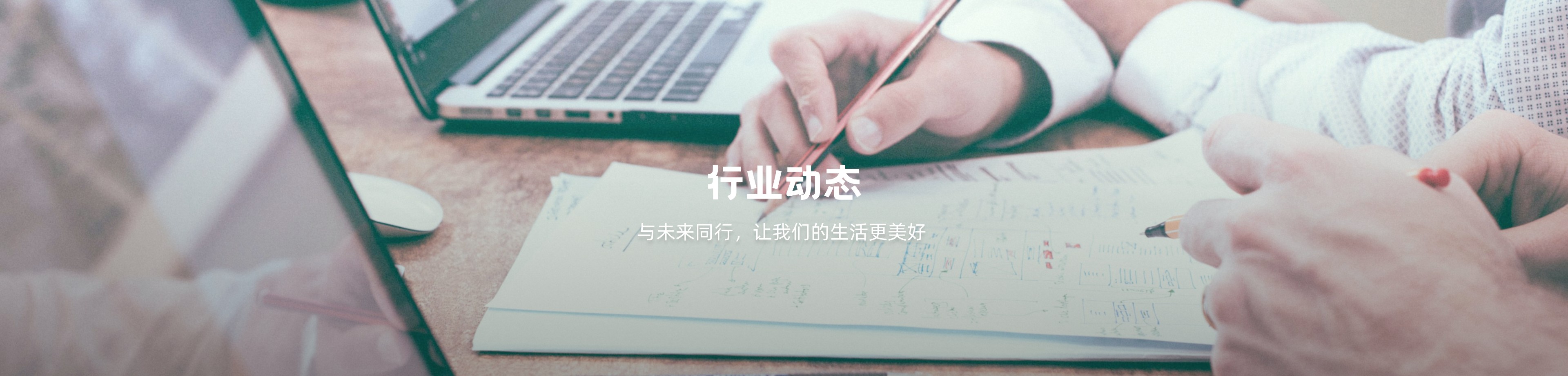商标是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而字号(字号是企业名称的组成部分,比如“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企业名称,其中“张小泉”就是字号)是区别不同企业主体的标志,其两者间功用领域间隔之纠缠,加之分管注册部门的不同,这导致商标与字号冲突不断的产生。
关于这类冲突的解决如何适用法律,无论是理论还是司法部门,一开始还都是非常没把握的,标志性案件应该是我的同事斯伟江代理的在上海二中院起诉的杭州张小泉诉上海张小泉案,这个案件当时引起一片讨论,法院好像还组织专家搞了一个研讨会,后经最高法院批复并在受理后近五年后判决。当然,经过这些实践与讨论,目前来看,是已经形成一定共识的,尽管有一些不断的反复与调整。基于这个原因,加之笔者从事的实务工作,因此,本文仅以一个律师的身份,结合我们代理的“张小泉”案、“埃美柯”案等判例,参考目前较有影响的判例,来系统的梳理一下该类纠纷处理在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目的就在于告诉同行们,如果我们代理这类案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希望对同行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冲突的类型
商标与字号的冲突,粗略的来讲,不外乎以下几种:
(1),在先注册的商标被他人后注册为字号。这类情形的案件,如上海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星巴克”案,原告星源公司在先在中国注册了““STARBUCKS””、“星巴克”商标,上海星巴克咖啡馆有限公司则在后以“星巴克”为字号注册成立;我们代理的“宁波埃美柯诉上海埃美柯案”[4]也是如此,原告宁波埃美柯在先注册取得“埃美柯”字号及商标,之后,上海埃美柯以“埃美柯”为字号注册成立。
在这一类型案件中,有的还同时存在恶意的突出使用“字号”,不规范使用企业名称,如前述“星巴克案”,法院认为,上海星巴克注册该“星巴克”字号本身构成不正当竞争,同时其简化使用“上海星巴克咖啡馆”、“星巴克咖啡馆”等还构成商标侵权。
(2),字号被他人注册为商标。这类情形的案件,多是一些知名甚至驰名的字号并他人注册为商标,如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泥人张”案件中,就涉及到被告北京泥人张艺术品有限公司还将“泥人张”文字注册为商标。另据悉,武汉同济已将“同济”注册为商标并通知上海同济有关医院不得再用“同济”字号(当然,它们好像还没有诉到法院)。这些都是字号被注册为商标的案例。
(3),字号的注册本身并不构成侵权,但一方滥用企业名称,恶意突出使用字号,造成与他人商品的混淆,侵犯他人商标权。如我们所代理的杭州张小泉在杭州中院诉上海张小泉案,杭州张小泉以上海张小泉总店在产品包装及产品上简化突出使用“上海张小泉”字样为由,认为其侵犯原告商标权,案件历经一二审,最终浙江高院维持杭州中院认定上海张小泉突出简化使用字号构成商标侵权的判决。
二,受理
关于已经注册的商标、字号之间的冲突纠纷可否直接由司法受理的问题,有文章说是“人民法院……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笔者认为,对于此,法院的观点确实是几经变化。粗略的来看,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院的观点是不直接受理。认为注册商标与已经登记的企业名称都是已经获得行政合法授权的“权利”,在行政未处理前,法院不便直接干预。
这个观点以“台湾蜜雪儿诉北京蜜雪儿案”为代表,该案一审法院北京二中院认为[8],“原告还指控被告为了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在北京不当登记带有“蜜雪儿”字样的企业名称,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使用“蜜雪儿”的企业名称。本院认为,被告的企业名称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批准的,虽该企业名称中的“蜜雪儿”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同,也确实会给普通消费者造成混淆,但如何调整这种关系,目前法无规定,且对企业名称登记的异议不属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范围,原告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请求。……”就此问题,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次阐明[9],“台湾蜜雪儿公司依法对“MYSHEROS”拥有商标专用权,北京蜜雪儿公司依法对其企业的中文名称“蜜雪儿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及英文名称“MISHER FASHION DESIGN(BEIJING)CO LTD”拥有企业名称权,双方各自拥有的上述民事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据此,任何一方当事人在没有启动行政撤销程序的情况下,即以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作为诉权基础控告对方当事人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内容侵害其权利均是缺少法律依据且有悖法理的。当事人对这类权利冲突的异议应先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解决。”
第二阶段,法院的观点是全面直接受理。认为司法最终审查是原则,行政的授权、注册不影响法院的受理及判决,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与商标、商标与企业名称之间的冲突,法院可以直接受理。
典型案件为“恒升诉恒生案”。该案“恒升”与“恒生”都是已注册商标, 一审法院北京一中院受理这个案件,并在判决书中写道,“虽然被告“恒生”商标已由商标局(2001)商标异字第1133号裁定核准注册,但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商标与原告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是否相近似作出独立的判断。行政管理机关的相关认定系从“恒生”商标是否应核准注册角度出发作出的,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在侵权诉讼中判断商标相近似性的依据。”、 “作为同行业的经营者,被告恒生公司在其后注册和使用商标时,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合理的避让。但其无视他人合法的、在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在相同的商品上注册并许可他人使用与“恒升”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其行为有失诚实信用原则。故虽然恒生公司于1998年9月21日后注册了“ASCEND恒生”、“恒生”文字及图形组合、“恒生”等商标,但由于这些商标均含有与他人在先注册及使用的“恒升”商标相近似的内容,从公平、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以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原则出发,被告不能以拥有上述商标专用权作为其不侵权的抗辩理由。……被告金恒生公司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与原告“恒升”商标相近似的“恒生”商标,这种行为使“恒升”商标的显著性、识别性降低,且在事实上给公众造成了混淆和误认,侵犯了原告对“恒升”商标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第三阶段,法院的观点是对注册商标提出的诉讼不直接受理,对企业名称提出的诉讼可以直接受理。
典型案例为江苏省高院二审之“同心纺机诉振泰机械织造案”,该案涉及原被告的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及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之间的冲突,此等纠纷法院可否直接受理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对此,一审泰州中级法院是直接受理并判决认为,“人民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涉案商标是否构成近似作出判断,同心公司所称振泰公司应先通过行政程序处理商标近似再行民事诉讼之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二审省高院却认为,“1、关于振泰公司和同心公司之间因各自拥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而引起的权利冲突纠纷,人民法院能否直接受理问题。本案中,振泰公司和同心公司均各自拥有一个合法的注册商标,且均未发现有超越授权范围使用商标的行为。振泰公司诉称同心公司所使用的“真泰ZT”注册商标与振泰公司“振泰ZT”注册商标近似,构成对振泰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其实质在于对同心公司“真泰ZT”注册商标的授权存在争议。关于此类争议的处理,我国商标法中已规定有一套完整的注册商标争议行政处理程序。

因此,主张权利方应先行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处理,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不应直接受理。据此,一审法院直接受理此民事纠纷不当,应予纠正。2、振泰公司针对同心公司将与振泰公司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振泰”作为企业的字号在商品上使用,给振泰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以及同心公司侵犯振泰公司企业名称权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
江苏省高院的这个裁定,其实是最高院的意思。因为,最高院在针对江苏省高院有关该案的请示所作之(2004)民三他字第10号函中批复道,“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商标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涉及注册商标授权争议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冲突纠纷,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中的文字相同或者近似的企业字号,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的,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审查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很显然,依据这个批复,目前的做法就是:首先,涉及注册商标授权本身的争议(就如上面的恒升诉恒生案),法院不能受理,只能到商标局通过行政程序了;其次,涉及企业名称登记本身的争议,法院可以受理,但不是按商标侵权而是按不正当竞争来立案;另外,除前述外,其他如针对注册商标未合理规范使用,针对企业名称没有规范使用损害他人注册商标权之行为而提起的诉讼,该批复中没有涉及,从法律规定及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可依照《商标法》的规定直接提起商标侵权的诉讼。这一点尤其要注意,是针对权利本身的异议还是针对权利的使用方式的异议,案由及法律适用是不同的,应该要分清楚。
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个批复,有文章批评他是“开倒车”。笔者以为,最高法院或许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吧,因为如果放开,等于全国那么多地方法院都可以修正商标局的授权了,从目前各地法院的公信及水平来看(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就可以看出),商标局会“受不了”,最高法院在说着“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原则”时恐怕也会有些信心不足。因此,笔者认为,最高法院这样规定也可以理解。不可以理解的地方是“批复”这个“立法”形式太隐秘以及法院在受理这个问题上变化太多。我们代理的一个注册商标侵犯著作权的案子就在上海二中院受理并准备开庭后又被法官“规劝”撤诉了。最高法院的“意思”变化太快,我们跟不上,法官也跟不上,都以为可以受理的,工作做到快要开庭了,又要求撤诉,等于白折腾,很是浪费。
三,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及举证
处理商标与字号权利冲突一般遵循:(一)诚实信用原则;(二)保护在先权利原则;(三)禁止混淆原则。北京高院《关于商标与使用企业名称冲突纠纷案件审理中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审理商标与使用企业名称冲突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保护在先合法权益的原则。侵权人的行为造成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和混淆,或者造成消费者误认为不同经营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或者对驰名商标造成《商标法》第10条第(8)项所说的不良影响,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停止使用企业名称或者对该企业名称的使用方式和范围作出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权利冲突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草案)规定,“审理涉及权利冲突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和公平竞争的原则正确界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在先权利
认为他人注册字号或商标的行为构成侵权,首先必须是自己拥有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或商标,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不是在先的权利,哪怕“后来者居上”(后注册的权利发展更好,知名度更高),你也不能禁止之前的权利人停止使用其字号或商标。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前提而已,无论是字号还是商标都不能因为在先而当然的排除之后他人权利的取得,你在先注册了“红光”商标并不当然的等于他人不能后注册“红光”字号或者“红光”域名,字号更是如此。
另外,一般来讲,在先的权利还需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是要在被告注册前而不是诉讼前就已经具有这个知名度。所谓“较高的知名度”是相比驰名而言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达到驰名的程度,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高度。怎样证明权利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从实践经验来看,一般可参照《商标法》、《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条例》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组织证据:一是,使用持续的时间,包括该字号或商标使用、注册的历史和范围的有关材料;二是,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包括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的方式、地域范围、宣传媒体的种类以及广告投放量等有关材料;三是,有关商标、字号的打假资料,一方面有人侵权,本身就可以反证有一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积极打假也证明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重视及维护成本;四是,包括使用该字号、商标的主要商品近三年的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利税、销售区域等有关材料;五是,字号或商标获得各种荣誉,这可以做为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直接证据。
在我们前面讲道的案例中,星巴克案是以驰名商标获得保护,而在我们代理的宁波埃美柯诉上海埃美柯的案件中,法院仅仅认定埃美柯在被告注册企业名称前就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些判决书在网上都有公布,建议同行们仔细看看,看看这些案中原告是怎样举证证明自己是驰名或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2)诚实信用
在企业名称与商标冲突的案件中,民法通则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诚实信用原则是重要的法律依据。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判断的标准是,一方是否具有“故意制造混淆,以图搭便车”的恶意。为什么前面说权利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笔者认为它也是为判断是否具有恶意,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服务的,因为,一个商标或字号,如果本身并没任何的知名度,那么,从主观上来说,无法解释他人“故意制造混淆,搭便车”的动机,客观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
至于怎样来举证证明被告存在“故意制造混淆,以图搭便车”的恶意?这还真不好说。概括的来讲,就是原告必须通过证据链来叫法官相信被告具有恶意。
在举证上,笔者总结:一是,前面说的证明权利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提供被告的经营规模,作一实力对比,这可以解释被告“搭便车”的动机。二是,提供被告(或者投资人等关联人)权利取得前和原告具有某种联系的证据,以说明被告的恶意。比如在上海一中院审理的伯特利字号与字号冲突案[12]中,判决即认为“被告的股东潘秀仁曾为原告的股东,被告在成立时应当知道原、被告系同业竞争者以及原告在企业名称中已经使用了“伯特利”字号这一事实,也应对原告的经营规模及发展有所了解。……仍然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伯特利”字号,其主观上具有搭原告“便车”的故意”,显然,这里面被告的股东曾为原告的股东这一事实就很关键,因为,他足以排除“不存在恶意的巧合的重名”这一情形。三是,被告注册该等权利的用途是什么?有没有实际经营?比如:南京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摄影店在南京注册字号,在南京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被告则是一家之后在上海注册的相同字号的摄影公司,它通过授权在南京开分公司,原告经调查发现被告在上海注册的地址经营面积只有8平方米而且在上海根本没有实际经营,而其主要的经营、广告宣传都在南京,原告据此认为被告的行为显然具有搭便车的恶意,在上海注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南京开分店以搭便车,法院采纳了原告的意见。实践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注册他人的字号或商标,并以此讹诈他人,作为原告,如果能收集到这一方面的证据,那将是非常有力的。 四是,被告是不是存在其他的明显具有意在混淆与原告产品的行为。比如我们代理的埃美柯案中,被告使用的产品手册与原告的几乎一样,而证据显示,是被告模仿了原告,这就很好的证明被告存在搭便车的恶意。五是,询问被告注册商标或字号的原因(当然这要求原告的商标或字号具有足够的“个性”)。比如星巴克案,主要一点就是被告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也取名“星巴克”。我们代理的埃美柯案也是如此,我们问被告为什么叫“埃美柯”,他回答不出来。注册一个字号或商标不可能无缘无故,必定要有一定的内涵,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个内涵,那是很容易被认定为恶意注册,故意仿冒的。
(3)禁止混淆
会不会产生混淆,这是一个重要审查点。如果原告被告的商标字号根本不会产生混淆,那么“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存在冲突及冲突解决的问题了。如果存在混淆,那么就是存在权利冲突了,至于冲突怎么解决,就要再依据前面的两个原则来做综合的判断。
怎么来判断“混淆”?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往往非常关键。笔者认为,一般来说,一是,应从商标/字号本身来看,其二者在文字内容,形式,读音,产品效果上综合分析,会不会让一个一般的相关公众产生混淆。二是,从权利双方的经营范围,产品类型是否相同或相类似上看。阐述怎样判断“混淆”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上面是解决商标与字号冲突的基本原则,作为律师,无论代理原告还是被告,都应该围绕这三点进行举证或反驳,其间的工作,对原告代理人来说,尤为艰巨。
四,判决及执行
(一)判决
在香港立时集团诉武汉立邦案[13]中,原告香港立时集团持有“立邦”注册商标,被告登记“立邦”为字号,原告认为被告登记该字号具有恶意,侵犯其商标权,故诉请“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变更以“立邦”作为企业字号,销毁含有“立邦”字样的侵权宣传资料、包装”。经审理,一审武汉中级法院判决“被告武汉立邦于本判决生效后下日内变更其企业字号,新企业字号中不得含有“立邦”字样”。这个判词的表达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责令被告变更企业名称,去掉名称中的“立邦”字号,但是,这个判词没有得到湖北高院的支持。二审湖北高院改判,“一、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武知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武汉立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得在其所有产品、产品外包装、产品宣传资料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立邦”文字”。理由是“因企业名称的登记和管理不在人民法院审判职权范围之内,故原审法院直接判决武汉立邦变更其企业字号不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显然,二审湖北高院认为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使用但不能判令被告变更字号,其理由就是这不是司法权力范围之内。笔者认为,其一、二审的不同观点,突出反映了法院对字号与商标冲突案件中应该怎么判决的分歧,其核心也就是对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的认识问题。对此,有文章总结说,各地法院主要有这么几种判法:
(1)判令侵权人对该企业名称或其字号的使用方式和范围作出限制;
(2)判令侵权人不得继续在其产品、产品外包装、产品宣传资料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某某文字。
(3)判令侵权人停止使用并责令变更企业名称或其字号。
对于这三种判法:
第(1),它实际上不是针对字号本身而是针对字号的使用方式作出的,如果原告对被告登记该字号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异议,而只是认为被告没有规范的使用字号,那么,这样的判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原告是针对被告登记字号之行为本身存在异议,而提出的诉请也是要去掉被告名称中的该字号,法院这样判决就是“偏离诉请”,没有正面回应原告诉请了。
第(2),也就是湖北高院的判法,笔者认为它让原、被告都很尴尬,对原告来说,被告的字号还将继续存在,他不能申请法院强制变更被告恶意注册的字号,其权利似乎并没有得到救济;对被告来说,法院未责令其变更字号,但是,这个不能在经营中使用的字号,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有观点说,原告可以持该判决书再到工商局去申请责令被告变更字号,这还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不过,司法的判决还要通过附加一次行政行为去落实,这是什么原则?
第(3),笔者认为这个判法能根本解决纠纷。而且,笔者认为,其并不存在司法入侵行政的问题,因为这里法院责令的对象是被告,是要求被告到工商行政部门去申请变更字号,法院并没有直接责令行政机关,这和法院判令被告去办理房地产过户等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笔者认为,湖北高院着实是“过滤”了。实践中,从上海法院的判例来看,其是持第(3)种判法的,在我们代理的“宁波埃美柯诉上海埃美柯”案中,一审上海二中院判决,“被告上海埃美柯公司停止对原告宁波埃美柯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含有“埃美柯”字样”,二审上海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不过,同类的案子,在“伯特利”案中,上海一中院的判词是“被告上海伯特利阀门有限公司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伯特利”字号、损害原告伯特利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表达上和上海二中院的判词似乎有些区别,但是,笔者认为其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核心都是责令被告停止在企业名称中继续使用某字号而不是如湖北高院只责令被告不得在经营行为中使用某字号。
上面讲的是判决,那么作为律师我们在起草诉状时应该怎样来提出诉讼请求呢?对此,笔者认为,这也要分成两种情况,第一,对被告注册企业字号本身没有异议,但对其不规范的使用字号有异议(比如,我们代理的在杭州中院起诉的,杭州张小泉诉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案),如上所述,依据最高法院的批复,这类案件属于侵犯注册商标权纠纷,因此,我们的诉请就表达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在……(产品、包装)上突出使用……字样,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的行为”。第二,如果是对被告注册字号本身存在异议,那么,依据最高法院的批复,这属于不正当竞争纠纷,在我们代理的埃美柯案中,原告诉请就表达为,“请求责令被告停止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执行
商标与字号冲突案件的执行也是一个难题。据悉,著名的“星巴克”案在执行的时候就很是艰难了一番。难在哪里?难在法院与工商局的协调上面。法院判决是停止使用某某字号,那就是要撤销旧的字号注册一个新的字号,如果被告不主动配合,怎么办?法院、工商局也不能直接给他取个名字,然后帮忙注册了啊。关于此,《上海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是这样处理的,“人民法院判决企业停止使用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并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登记机关应当通知该企业在三个月内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企业未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的,登记机关可以对该企业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都是法律专业的,按照他这个“法律”,案件怎么个执行法?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觉得这类官司别打了。打了也白打,这不可能,法院总有办法可以执行的,而且就算当年执行不了,第二年年检的时候,工商局应当是不会让它通过的,这实际也等于是执行了的。
其实这类案件的执行,我认为,它并没有什么无法跨越的理论或立法问题,无非就是工商局的态度。我认为,法院给工商局发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工商局就只需等被执行人前来办理名称变更申请(我认为,根本不需要象上海的规定那样,再发一个什么三个月的通知),法院指定的期满以后仍没有来,那么,旧的字号不能用了,新的字号,被执行人不提供,这就等于是没有字号了,没有字号就是没有企业名称,就不符合企业设立的基本条件,直接给他注销就是了。
据消息灵通的同行披露,“近期最高院将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共同发文,此类问题可望得到解决。”相信会有一个办法,否则,判决不好执行,总是有损“司法权威”的。
五,结语
因为办理案件,笔者看过很多相关判决,经过办理几起案件,又进一步积累了实践的经验,更清晰的掌握了法官对此类案件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在商标与字号冲突类型案件的处理上,笔者有一定的实践积累。现在,利用业余时间将这些积累整理出来,相信能对同行们有一些作用。
作者:吴鹏彬律师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